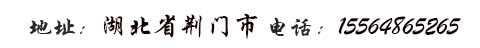把河西喝醉四
|
瓜州 夜宿玉门的那晚,喝酒喝到飘,第二天一早去瓜州,年之前,它的名字是安西。 从玉门进入瓜州,是西部片一样的世界,茫茫荒山,连绵起伏,少有人烟。 跑上山顶,吹着来自西部群山的风,脚下全是褐红色的砾石,太阳耀眼,在这种地方,你走上几十里都很难看到人烟,当水源不再,人类便会搬离,路旁有一处土堆,大约是从前有人居住过。远处的沙柳在秋天变红,像一道红色的河流。 在茫茫戈壁群山中走了很久,我们来到锁阳镇,这里现存著名的锁阳城遗址,并出产最好的锁阳。 在锁阳镇吃午饭,这是一个安静遥远的西北小镇,人们放羊,在少量的绿洲上种植庄稼,秋阳照在小镇唯一的一条街道上,蔬果店的老板在门口剥蒜,我走过去和他闲聊。 小镇街道的中心有一座亭子,上面写着四个大字“疏勒绿洲”。 满眼都是我所爱的西北,以及我梦中的通往西域的河西。 饭后我们沿遥远笔直的戈壁公路继续前行,去往位于榆林河边的榆林窟。 一座保存最完好的古城(我至今在河西所看到过的)猝不及防地从窗外闪过,我跑下公路去看,真的是一座古城,四面墙体基本完好,城内有残存的土垛与矮墙,地上长着些顽强的沙漠植物,看起来不知是死是活。城堡中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破城子遗址”,是魏晋时的常乐城,它所在这个村子现在叫常乐村,古城没有被圈起来作为景点售票,它很平常地存在于戈壁上的村落旁,不是走近了去看,你很难想到它是一座建立于魏晋的古城堡。 听说城内散见陶片瓷片铜钱铜箭头,因为赶路,我没有仔细在城内走上一圈。 我心心念念一直想去的高台骆驼城,最后也因为急着赶路没去成,听说当年清理骆驼城遗址时,发掘了几吨的铜箭簇和古钱币,年有人到骆驼城时,内城里还能捡到开元通宝。 从河西回来的时候,我只捡了一堆石头,摘了一袋棉花,还有几根毛蜡烛。 路遇破城子的那天我很感动,感动于时间的流逝,穿过千百年的历史,我还能够在此刻的秋天里站在汉魏旧城下瞻仰历史的痕迹,尽管如今它只余破损的墙垣,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凭借想象力去还原它远在公元前的历史中车马往来的热闹场景。 它的名字那么好听,常乐城。他们生个公主要叫常乐,设立边关郡县也要取名常乐。 以前每到江南,走过苏杭旧地时,我总会觉得满眼都是宋词,而当我走在河西大地上时,眼里又都是汉唐的边塞诗和戍边史。 榆林河边的秋天来了,山下的树叶全都黄了,河水很冷。 相比莫高,榆林窟基本是安静的,平时少有人来。 托老刘的福,我们有幸得以看到榆林窟中的几个特级洞窟,并享受了整个榆林窟中级别最高的讲解服务。 为我们讲解的男孩儿很年轻,姓邢,定西通渭人,笑起来特别好看,又那么谦逊,他说大学念的是历史考古专业,后来写过一个关于河西走廊壁画洞窟的文章,因此得以到瓜州县文物局工作,新近又考到了敦煌研究院。 从去年开始,敦煌研究院将甘肃省从东到西的几个较大的石窟纳入其管制下,其中包括榆林窟。 我们叫他小邢,从心底里佩服他,像他这样年轻的人,能专心去做石窟壁画的研究,在这样一个地方,耐得住这样的寂寞。 他打开每一个洞窟的门,为我们做详细的宗教、历史和绘画讲解,长达一个多小时,国庆节期间,他们是全员满班,像这样的讲解,他每天要接待七八个。全程没有用扩音器,他说是为了让参观者听起来更真实舒服一些。 从洞窟出来,他微笑着向我们鞠躬致意。还有一位大姐,也微笑着同我们道别,那样谦逊、温柔、优雅,如沐春风。他们是我对榆林窟产生好感的一部分,当我们聊起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樊锦诗时,他们亲切地称呼她为“我们院长”,难掩自豪的亲切和喜爱。我记得在某一个洞窟中,小邢用手电筒打亮一个白描飞天,开心地说“这是我们樊院长最欣赏的飞天形象。” 从常书鸿、段文杰到樊锦诗,再到为我们做讲解的小邢,从国立敦煌研究所到现在的敦煌研究院,几代莫高人的青春都在这里,欣慰的是,外面的世界再闹腾,这里的精神还在。 那天在榆林窟,我们看到了以青金石做颜料绘制的两幅水月观音,各种情态的菩萨和佛陀,后世的供养者,历代河西望族的画像,以及轻盈流动的飞天。 而我最喜欢的还是一处展现尘世生活的图景,它被画在某张壁画的左下方,是秋天收获的场面,人们从地里收割谷物,谷场上有人打谷,之后借着风力用木锨将谷物高高扬起,脱去谷衣。在画面中,谷物是用褚色颜料画上去的,我猜他们收割的大概是糜子。 小邢说,这是一幅魏晋壁画。 我完全被那个场景打动了,它让整个河西的洞窟壁画不再只有缥缈的往生与来世,它形象地记录了几千年前的现世生活,那种劳作场景绵延了前年,在今天的西北,秋天里的人们仍在用这样的方式收获谷物。 一种世代相传的古老农耕文明的味道,就在那一刻扑面而来。 在榆林窟时,我问过小邢关于破城子那样完整的古城为什么没有被保护起来,他告诉我,单在整个瓜州境内,就他所知道的类似破城子这样的遗址还有不下五十处,太多了,很难兼顾,他们曾经尝试捆绑申遗,但没有成功。 我说我一定会再回来,我要用足够的时间去寻找那几十处遗址,我有太多的问题要向他请教。 这种喜悦伴随了我一整天。 榆林窟去往瓜州的路上,我们在半路被拦下来接受检查,据说前方村子曾发生过疫情,当下是高发季节,所有进出的人员都要接受检查。 类似的瘟疫也曾在玉门发生过。 敦煌 瓜州去往敦煌的路上会路过那个叫“悬泉置”的地方,尽管如今它只剩了一个考古挖掘现场,我还是很想去看看,我执念于公元前52年左右,常惠多次路过悬泉置出使乌孙及西域诸国的那段往事,以及悬泉置里那位负责接待工作的名叫吝啬夫的边关戍守者,解忧公主和亲乌孙,常惠出使乌孙,以及他后来护送大汉的另外一位公主再次和亲乌孙,嫁于解忧公主的儿子元贵靡,都曾在悬泉置驻留,在吝啬夫的每日边关事务簿上,记载了往来人马,伙食,宴饮。 而后来我所看到的悬泉置,只是公路边某个一闪而过的标识牌。 黄昏时我们来到敦煌,并没有去市区,而是直奔莫高窟,范想要爬上三危山一览夕阳万丈光芒下的莫高胜景。 可惜国庆节景区封路,我们在通往莫高的路上被工作人员劝返,太阳开始跌落地平线,它变得越来越圆,橙红明艳,当我们到鸣沙山下时天已完全黑了。 这里和从前大不一样,文博会之后的敦煌发展惊人,除了鸣沙山前的这条公路依旧和过去一样笔直外,我找不到其他任何相似的东西了,道路两旁从前是些当地人的村落,树林和田地,我们到达的那个晚上,公路两旁一片灯火,客栈、卖纪念品的店铺,以及各种茶馆酒馆餐馆,上行和下行的车辆堵满了所有车道,交警正在路口卖力地维持秩序。 我们把车开进村落深处,停在一处村委会的建筑门口。 是时九点多,我们乘着月光往鸣沙山下走去。 多年前的一个冬天黄昏,我也是从这个村庄里爬上了鸣沙山。 那晚一片暗黑里,我居然也找到了多年前走过的那条路,山下比从前多出了一道铁丝网。 那天是中秋节之夜,我们在鸣沙山下翻越铁丝网,就着月亮的清辉开始爬沙山,那道沙山的山脊还是那么陡峭漫长,沙子上留有白天太阳的温热,我们脱下鞋子,绑起来,挂在肩上,在沙山上艰难地往前走去。 终于爬上山顶那一刻时,像多年前那样,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弯如新月一样的湖水,头顶是中秋节的一轮圆月,沙漠上的月亮又大又亮,身后是闪耀着万千璀璨灯火的敦煌城,山下传来的人声耳语,远处沙漠里露营者星星点点的帐篷,有风吹过来,风里扬起的细沙吹到脸上,嘴里。 我想起许巍的一句歌词“如幻大千,惊鸿一瞥。” 这是那一刻我站在山顶的全部感受。 我们几个突然都变成了温柔又沉默的狗,老刘默默地在月亮下点了一支烟,三金唱起了她的“明月几时有”。 我躺在沙子上,吹着风,看看月亮和泉水,无人可想。 也许过往的确都变成树叶顺流飘走了,沉渣烂柯也没有了,当我再一次想要分享眼前的大山与大河时,却发现无人可想。 “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 那晚我们在沙山上坐了很久,回到市内已是深夜,又去吃羊肉又去喝酒,睡眼朦胧地喝完了酒。 敦煌城是我的梦,不是从前,不是现在,是我四十岁后的梦,四十岁后再听着“越过山丘,无人等候”的歌,在另一轮明月下。 多年前我写过唯一的一篇不能称为小说的故事,关于敦煌,一个远嫁的女子,少年故交,大漠西域的余生。这也是我之所以从一开始就喜欢常惠与解忧的原因,他们就像我曾写过的那个故事的现世版。 那是一种神奇的缘分,让我得知这世界上真的曾有那样的人和故事发生过。 第二天清晨我们去往阳关,那里有我多年前曾无意看到过的一片湖水,以及我想死后归葬的地方。 敦煌去阳关的路现在修得很好了,公路在广阔的戈壁滩上延伸,看不到尽头,路旁除了戈壁,空无一物。 阳关镇外二十余里的一处地方,戈壁荒滩,矮矮山包,是一处坟场,里面散布着零星的坟堆,那时是冬天,我站在那些矮山中,看着那片辽阔雄浑的大地,西望阳关遗址,对当时身边的朋友说,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就把我埋在这里,每年杏花开的时候,我爱的人会从东边的故乡远道来看我,提上一壶酒。 而当我再一次站在那里时,周围则是新建起来的一排排用以晾晒葡萄的阴房。 阳关种植葡萄的历史有几十年了,现在葡萄已成为每一户人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和唯一经济作物。 绿洲出现的时候,道路旁长满了笔直的白杨,就是多年前我曾在冬天走过的那条路,那时我想过我还会回来,一定要在秋天。 我果然在秋天回来了。 阳关镇西行十几里的尽头,是一处湖水,名叫“渥洼池”,相传汉武帝当年曾于此求得天马。 秋天的渥洼池水位下降,湖边古树遮天蔽日,只是叶子还没变黄,白色的水鸟自湖上掠过,一群脏兮兮的羊走在湖边,远处是大片大片望不到头的芦苇丛,芦苇低矮,叶子锋利,秋风秋阳里,它们发出簌簌的声音,白色的芦苇花闪耀着银色光芒。 那真是一片忧伤的芦苇荡,宁静遥远,我们不来,只有风和阳光。 那年我从阳关镇借了辆自行车一路骑到这里,冬天湖面结冰,冰面顺着水流一直延伸到人家的田地旁,水库下的第一户人家那时养着几头驴,现在他们正在摘葡萄,这种葡萄被称为无核白。我们和主人聊天,寻找葡萄架上没有摘掉的零星小葡萄,它们被晒得发黄,很甜。 下午我们在沙洲市场再一次吃了一顿炕锅羊肉,真是百吃不厌,我恨不得一口大锅里全上满羊肉。 白天要行车赶路,不能喝酒,河西八天,醉酒每在夜深人静时。 张掖 敦煌后开始返程,一路奔袭未能赶在天黑时到达张掖城,只好留宿酒泉。 约了Z,撸串喝酒,这次喝的是黄酒,酒精度太低,谁也没飘起来,夜游酒泉,中心有一处鼓楼,东西南北四向分别写着: 北通沙漠、南望祁连、东迎华岳、西达伊吾。 车过高台,一想起去不了的骆驼城,我就很难过。 我对高台最初的兴趣来自于出生张掖的新晋导演李睿君自编自导的一部小众电影《在那水草丰茂的地方》,影片讲述了一种文明消逝的哀伤,我认为这种哀伤是贯穿河西的,它不只是裕固人的心理感受,它应当属于我们所有人,旧的文明,建筑,文化,信仰,村庄,生活方式……一切都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消逝,就像水源一样。 车过张掖城时,我想起了大学时的好友W。她约我在张掖见面,喝酒,而我依旧因为要赶路没能去见她。我们最早见面是在04年,她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来自河西人的厚朴和善良。 出张掖后,我们一路向着祁连山的方向前行,越来越近,眼前的山变得巍峨高大,山顶的皑皑白雪在阳光下发着光,祁连山下的人家,房屋与古树,路边的孩童与老人,道旁杨树的叶子黄了,地里有打包机正在将谷草打包,我们路过的小镇小村落,因为所处偏僻的缘故,几乎没有受到甘肃省近几年“新农村建设”的影响,都很好地保留了当地古老的村庄建筑原貌,高墙拱门大院。 在一处河流前,我们停下来,河道已经干涸,也许这是一条季节性河流。河道里有一种纹路奇特的石头,废旧轮胎,报废的淘沙车,河岸上有一座古城的遗址,有人在崖壁上凿洞穴居住。 那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叫临松薤谷,那是一个我第一眼看到名字就喜欢上的地方,虽然我并不大理解这个名称的由来和含义。 在河西走廊的历史上,曾有三代大儒在此居住、讲学,也有马蹄寺石窟群这样的佛教建筑与壁画艺术。 对当时第一个来到这里的儒者郭荷来说,也许它足够清净,是潜心修学的好去处。 临松薤谷这个名字,则因为他们三代师徒而被更多的人所知晓,吸引了许多河西子弟纷纷前来求经问道。 当我们走进临松薤谷时,眼前是一个藏汉混居的小村落,村子就在祁连山脚下,尽头是马蹄寺石窟的入口,这是一个涵盖范围很广的石窟群,洞窟沿山体开凿,内有残存的壁画、佛像、塔雕,和河西其他石窟建筑不同的是,马蹄寺石窟至今有僧人修行,香火旺盛。 石窟凿在崖壁上,连通洞窟之间的通道就隐藏在山体内部,狭窄幽暗,需要踩着前人留下的足迹手脚并用地爬上爬下,国庆假期洞窟前排队的人很多,老人小孩儿,大多时候人们对幽暗通道尽头的好奇往往大于他们对佛文化和石窟艺术的热爱。 让我失神的是山上的一处佛堂,一个很普通的洞窟里,有七八座菩萨金身像,地上摆满了僧人们诵经时所坐的蒲垫,却空无一人,只有诵经声在山洞中回响,我听不出他们所诵的是哪一部经书,我迈不开步子,世界好像一下子空寂了,安静,空旷而寂寥。 我只是怔怔地站着,站着站着眼泪就出来了。 那一刻的光线、气息、声音、温度……所有的一切好像都在对我说:归来吧孩子。那种声音缥缈,虚无,却又穿透一切,那样悲悯,包容,它化我的精神铠甲、我的骨骼构架于虚无,它一眼看穿我身上的执念和苦难,我就像出走时那个赤条条的孩子一样,走了回来,站在它面前,两手空空,两眼热泪,空无一物。 远洋在门口喊了我一声,我起身,回过头,走向门槛,那一眼是万千世界灼人的光,远处是祁连雪山,山上的树木叶子正在变黄,色彩斑斓,山下经幡飘荡,庙宇的铃铛在风中抖动,脚下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我对远洋说,我刚才有种特别不好的感觉,我觉得它就是我将来要回去的地方。 临松薤谷对我来说,是个不能解释的神奇存在,是出发前、路途中我最心心念念的地方,河西有那么多的好去处,祁连山里有许多幽深僻静的地方,我偏偏要执着于走一趟马蹄寺。 就像这世间有那么多条路,路上有那么多人,而我,却偏偏要向你去问一条路。 张掖去往西宁的西张公路很美丽,沿途尽是遥远而有古风的村落,在翻越祁连山前,道旁秋日风景如画,密密的杨树随着车行急速地向后退去,满树金黄,真想跳下车去在这样的路上散个步,一直走到天黑。 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又回放了一段那一天走在祁连山下的视频,道旁后退的白杨,阳光把叶片打亮,视频里有我们的欢歌笑语。 当我们到达著名的扁都口时,天色已黑,眼前就是高峻连绵的祁连山,起伏的山坡上牧草已黄,我们进入峡谷,走上了一条长达四小时翻山越岭的道路,天色暗黑,看不清祁连山的样子,天下着雨,雨后来变成了雪,雪粒质地坚硬,拍打着前车窗,“祁连六月雪”,我想起隋炀帝当年西巡翻越祁连山的盛况,以及他们后来所遭遇的暴风雪。 我们路过俄博岭垭口,路过岗什卡雪峰,夕阳在远处的山头上变作了火烧云,红红地烧了起来,等天彻底黑透了,前方又是一轮明月。 当眼前的道路变得平坦时,我们到了大通河谷,西宁近了。 四个多小时后,我们把祁连山留在了身后,我们探访河西历史、地理、自然和文化的旅程也就在那一刻结束了。 而这座山,才是我们此行最大的目标和意义。 如果没有祁连山的冰川融水所造就的河流,北部的内蒙大沙漠就有可能连通柴达木盆地的荒漠,那样就不会有河西走廊,也不会有丝绸之路。 祁连山是河西的生命之源。 我热爱河西四郡,更想致敬这样一条山脉,虽然我们只是在暗夜里翻越重山,我总觉得有一天还会回去,还是要在牧草转黄的时候,在艳阳天里走走这条路,尽管已是不同的人和心情。 西宁 天黑进西宁城,城里灯火璀璨一片,我们一起感叹这夜景真美丽。 西宁城有我二十几岁时最无知无畏的青春光景,而此刻归来的深夜我却只能喝上一杯名叫天佑德的青稞酒,把自己喝到飘,和三金吃了两个猪脑子。 深夜的西宁,吹过我脸庞的是十月的风,风里我还能想起蚂蚁沟水库那些年夏天吹动裙裾飞扬的风,那些清晨和黄昏啊,虽然没有深夜饮酒,可你仍能笑得像满月。 清晨的莫家街,我们吃了一碗羊肠面,还在市场口第一家,唯一没变过的是这羊肠面的味道,我吃着羊肠面,突然想起某年夏天黑马河小饭馆门口的一张笑脸,笑得像太阳,想起某个雨声滴答的夏夜的长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没去过武汉,也再没见过像太阳一样的笑脸。 从西宁回兰州的路上,我再一次睡着了,醒来时车过河口。 想起有一年夏天,大学的男闺蜜带着我们仨去西宁,车停在莫家街吃饭的时候后视镜被人刮掉了,我们买了一卷胶布,把镜子勉强粘上去,路上总掉下来,然后就一路用手托着,半路下起雨,我们仨都睡着了,他一人开着掉了后视镜的车,在大雨里回兰州,车过河口,我们都醒了。 那年夏天在黄河边喝完茶后我们就没有再见过,后来我们越走越远,直到失去联系。 兰州 从前关于兰州,我们有一帮少年。现在关于兰州,我能想起的只有Z。 当我在国庆假的最后一天自西向东走出兰州时,她正穿越大半个城市回到黄河对岸的家里。她是这些年里无论我变成什么样子都始终坚持爱我的人,我从无知到莽撞,从怯懦到一腔孤勇,她都能站在一个离我不远不近的地方,鼓励我,支持我。 我从前狭隘自私,对人傲慢无礼,却又常常陷入抑郁,有时薄情寡义,疯疯癫癫。Z从未因为这些而质疑,她远远地看我哭,看我笑,就像看着一个跌跌撞撞、不知如何去长大的人。 我不大懂得怎样去维系情感,太粘腻的关系容易令我感到疲倦和压力,冷淡又会令我产生疏离感。Z比任何人都懂得拿捏平衡,和她在一起,我不用刻意去收敛或者表现,也不必担心自身的不美好。 从某种层面讲,她比我自己更了解我。多年前在黄河岸,她曾说我是属于田园和山水的人。她更清楚我适合什么样子的生活,而我更多的只知自己喜欢什么,却从未思考过自己适合什么。 Z不能算是漂亮的人,事实上,她一点都不漂亮,但她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她是我所认识的情商最高的女人,那是一种基于男人情商而存在的心理能力,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情商概念。如果她是个男人的话,她可能会拥有远比现在更高的平台和成就。 但是她结婚了。 她选择婚姻不同于俗世普通女子对“幸福”的追求,她认清生活的真相,并义无反顾地走向它。这是我所不能做到的。 她结婚的那个夏天,我远上兰州,做了一次伴娘,那也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做别人的伴娘。 我们相识在十三年前的汶川,那时这个远在川西横断山脉边缘的小城还没有以一场八级地震而闻名世界,高山阻隔,遥远偏僻,在十八岁的我眼里,简直是幽闭身体和灵魂的人间牢笼。我想她当时一定看见我哭了,虽然那并不是我最怂的时候。她给过我许多鼓励和善意,虽然我们都是不善于表达私密感情的人。 端午节时,她休假从兰州来看我,我带她走过六盘山、关山和小陇山,当我们走在夏日的郁郁山间时,更多的是沉默无语,那是一种不说话也觉得很舒服的默契,她是个积极生活、工作的人,不像我,她是优秀的女儿、妻子、姐妹,她没有时间去浪迹天涯,一年里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无怨无悔地加班,她希望我远走天涯,也希望我嫁人生子过上幸福的尘世生活;她希望我在山水间做个明亮的人,也希望我能用短疏浅学换取浮名一把。 从我认识她开始,她总是在积极认真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她身边的师长、同学、朋友、领导们喜欢她,信任她,因为她几乎比任何人都靠谱。 我对绝大部分的女人缺乏兴趣,而Z是我真正欣赏的人之一,她几乎拥有男人的智慧和情商。 我曾想过要专门写一篇关于她的文章,可是今夜当我写到兰州时,我无法绕开她。 平凉 最后一天晚上,老刘的朋友半路设宴招待我们,席间喝的是陇南金徽,平时深不见底的老刘和范却都飘了,我酒没少喝,但最终也没能飘起来。 我们穿过迷雾笼罩的六盘山,路上下起小雨,山间起雾,雾气铺满道路,两个醉酒的人在后座掏心掏肺地互诉衷肠,互相晾晒自己柔软的肚皮,我放了一首秋天的歌,夜色中的山影像青黑色的兽脊,有那么一瞬间,我放松警惕,松动全身铠甲,探出头来,想做个幸福的人,就像那一刻雾气缠绕的山间,缥缈得无踪无形。 是夜,窗外雨声滴答,一直到天明。 “人生不能太过圆满,求而不得未必是种遗憾。” 他们走后,我躺在一个雨天的床上睡了一整天,醒来时哭泣,哭完又沉睡,在我的前半生里,第一次懂得了温柔的意义。 我从前的确是个特别不好的人,我和范相识多年,他令我看到曾在执迷中挣扎的自己,老刘是我的围棋师父,他使我懂得了另外一种智慧,三金和远洋让我明白心怀善意和温柔是多么可贵的品质。 很难想象,这种领悟和习得来自最广袤粗粝的河西。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所有的结局中,这是我最钟爱的。 图/文 Alesha 苹果打赏 戳 赞赏 人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uoyanga.com/sytp/1447.html
- 上一篇文章: 甘肃美丽县城河西篇确实很不错
- 下一篇文章: 想懂完整的经方那一定得学金匮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