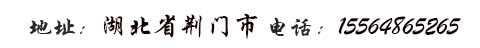No原创听路上故事杨献
|
主播:萧秋水 后期:淡颜 作者:杨献平 这当然是一条著名的、伟大的,贯通古今中外、光华灿烂的道路,德国人李希霍芬把它称之为“丝绸之路。”相对于这条道路形成的历史,李希霍芬的命名是短暂的,但学术界却异口同声、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它。丝绸之路,伟大而浪漫的名字,从古老的中国一直延伸到埃及、地中海沿岸,甚至出现了史前时期的法老的墓葬。在历史蒙昧时期,丝绸与黄金等量,是另一种货币,通行和风靡于整个欧亚大陆。尽管十字军有过东征,尽管丝绸路上其他民族也掌握了这项技术,甚至在高仙芝甚至整个唐帝国在“西域”遭到彻底失败的“怛罗斯之战”时期被俘虏的,中国唐朝军士杜环带着中国的技术,沿着欧亚大陆向西直达波罗的海,然后由海路返回。在他的《经行记》当中,记载了一个中世纪的中国唐朝人,在世界上的孤独的行迹。正如法国的于格叔侄在其《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一书中所说:“每一个前往丝绸之路的人,归来时总是与众不同。”这句话的间接意思是,凡是动身去到伟大的丝绸之路上的人们,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归来之后,他们都携带了无尽的传说,也经历或者创造了某种奇迹。因此,古老的丝绸之路向来就是创造奇迹的地方,更是文明和物质,流转世界的早期通道,尤其是在海洋横亘于人类的脚步之前的那些年代。雪山、大漠、驼铃、绿洲、湖泊、草原,以及暴风雪、尘暴、雪崩,马蹄上的骑士与冷兵器,商旅眉毛上的尘土,干裂嘴唇上的血渍、和亲者的车轮,卷起狼烟的战斗军团、游牧队伍……犹如蛇群奔行一般的白尘,啃食苜蓿的汗血马、跳胡旋舞的异族歌姬、出塞作战的诗人、凶悍的盗马贼、杀戮的弯刀、诵经的僧侣……如此等等,“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峰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多少诗篇汇集的博大与悠远之地,构成了丝绸路上最为璀璨的光辉,并且与日俱增,一直普照着人类的今天。从古长安出发,越过秦岭,进入伏羲之地,再兰州,渡黄河,乌鞘岭宛如剑鞘,山顶的白雪似乎人类内心绵延千年的哀愁。河西之地,做过国都的凉州,李世民家族的发祥地之一,再向西行走,迎面而来的大戈壁像是一块巨大的生硬的铁板,赫然横在眼前,给人以迎头重击。荒芜之地,向来与死亡紧紧关联,瀚海泽卤,象征着某种人生甚至人类的绝望和沮丧。可是,早些年间,这里完全不是现在的样子,至少有水源、草地、树林,虽然一直在风沙中被侵蚀,但仍旧有人在这里生存和居住。周朝的时候,这里的民族被称为西戎。这个名字现在听起来陌生而又带有诗意,可在周人眼里,却是经常骚扰他们边境,劫掠财务,居住或者游牧在西边的蛮夷之族。即《祭公谏征犬戎》中所谓的“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是也。《诗经﹒采薇》也说:“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岂不见戒,猃狁孔棘”,《孟子·梁惠王》亦有“太王事熏鬻,文王事昆夷。”等句。在金昌站下车,回身一看,就可以看到一座大山,上半部分洁白而苍茫,下半部分则显得黝黑,且沟壑纵横。这就是祁连山。出自匈奴语系,意思是“天山”。“天”就是匈奴信奉的最高的神。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中说:“像斯基泰人一样,匈奴人基本上是游牧民,他们生活的节奏是由他们的羊群、马群、牛群和骆驼群而调节。为寻找水源和牧场,他们随牧群而迁徙。他们吃的只是畜肉(这一习惯给更多是以蔬菜为食的中国人很深的印象。)衣皮革,被旃裘,住毡帐。他们信奉一种以崇拜天(腾格里)和崇拜某些神山为基础的,含糊不清的萨满教。”西方学者大部分带有不可掩盖的傲慢,这在他们对于中国的叙述和观察当中,时常会出现。勒内﹒格鲁塞也是世界著名的学者,但其在叙述萨满教时候,体现出的口吻是轻慢和自以为是的。实际上,萨满教是真正的原生性宗教。它和基督教、道教、佛教等等完全不同的是,萨满教没有创始人,完全是在某种社会和自然环境下,人群自我发生的一种以神灵的崇拜和信仰为基础的宗教。就像相信昆仑山乃是万山之宗,也相信昆仑山是中国之“祖龙”“祖脉”所在。《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道教将之作为元始天尊和混元派的道场。这也说明,原始的万物有灵的信仰和崇拜,并只限于匈奴人,更不限只于中国人。为祁连山命名的匈奴人,他们以为天地自然万物都是有灵性和具备某种力量的,如庞大的山系、寥廓的牧场,以及身边的水流、巨大的石头、人难以攀登能力的巨大石崖,超出经验之外的树木,以及难以用常理和生存经验解释的人事物,都归于“万物有灵”。我不觉得这种信仰和神灵崇拜有什么不妥,特别是当人们处在蛮荒和蒙昧时期,产生一种基于身边万物,以及天地之间的有神论的信仰和崇拜心理,何尝不是对人心是一种安慰?好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乃至这个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无所不能,无所不可的程度。科学的越来越神通广大,技术能力的无孔不入,以至于人类的生活空间越来越趋于透明化。这当然是好事,同时也是悲剧。因此,用现在的眼光来观察山川河流,乃至整个世界的存在方式,人类的未来,以及诸多事物的内在性与发展性,已经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了。如对祁连山的考察和概括,已经不再像匈奴和古民族那样笼统指认了,而是以科学的方式,测算出它的具体长度和宽窄度。简要而说,祁连山东西长公里,南北宽到公里,平均在海拔0至米之间,其西端为当金山口,与新疆的阿尔金山脉相接,东端则衔接黄河谷地,秦岭、六盘山与其相邻。自北而南,分别有大雪山、托来山、托来南山、野马南山、疏勒南山、党河南山、土尔根达坂山、柴达木山和宗务隆山等多座高峰,其最高峰为疏勒南山的团结峰,海拔达到米。这一座宛若游龙的山系,至张掖肃南,便与今之金昌相接。也就是说,金昌乃至河西走廊的每一座城市,甚至村镇和沙漠戈壁,都是同气连枝,不可分割的。有赖于祁连山雪水的融化和潜行,才使得干旱的河西走廊具备了人居的基本条件。换句话表达,即,有了祁连山,河西才有人的存在,才会在丝绸之路兴盛时期,积攒和输送了那么多的文化和文明,即使在现在,祁连山仍旧是河西诸多城市村庄的母亲一样的存在。而转身过来,在金昌市的西北,是另一个高耸之地。它的统称叫做阿拉善台地。这一片处在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的绿洲——即便是被漫漫黄沙分割成为许多个小块水草地的荒芜之地,其历史也是深厚的。阿拉善这个名字,也出自匈奴语系,即贺兰山的音转。匈奴强盛之时,它的贺兰部驻牧于此。可以想象,贺兰山、龙首山、曼德拉山上至今留存的岩画,大抵也由匈奴人的痕迹。而靠近现在金昌的部分,则是匈奴休屠王的驻牧地。在秦始皇时期,这里名为北地郡。随后是汉武帝的胜利,这一带也尽入西汉帝国版图。每一块大地上,都浸漫着无数的献血,也都埋下了无数的骨殖。将士和边民,战争的胜利和失败,民族和民族,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胜败得失,都是以牺牲诸多的人命为基本代价的。在很多人眼里,阿拉善高地,只不过是一片荒凉的大漠瀚海,也只不过是一纸仓央嘉措的传说,以及关于弱水河的动人故事,还有额济纳每年十月的金色胡杨。而它的悲壮悲情历史,乃至也很深厚的文化底蕴,一点都不亚于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再论及居延汉简,阿拉善高原,也真的是人类的精神富饶之地。尽管它在很长的时间内,总是沉浸在无尽的黄沙之中,在形如深井的天空下,与狂浪无际的风尘沙暴、发菜、锁阳、苁蓉、甘草、双峰驼及肥硕的牛羊一起漫步于浩浩荡荡的时间。作者介绍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现居成都。 蓝素有约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uoyanga.com/syyx/11000.html
- 上一篇文章: 营养识堂ldquo春韭一束金r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